奥运是一场盛大的狂欢,连平时对体育漠不关心的人都免不了被热情感染而将目光投向这力与美的博览会。然而在奥运村里,这狂欢却有个外界难以想象的主题——性。

每四年一度的盛夏时分,奥运村就成为了超过10000名运动员的临时家园;就算在参与人数较少的冬奥会上,奥运村也会容纳2700名左右的冬季运动员。这里聚集着这个星球上在各项运动上最有才华的人,于是它便自然形成了世界上门槛最高也最排外的精英俱乐部。在外人看来,这些精英除了要有惊人的身体天赋外,还必定兼具为了更高更快更强而将人类体格能力推到极限的拼搏精神。
直到最近20年,奥运选手这种苦行僧的形象才出现了裂痕,甚至有了大逆转的苗头。1992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主办方“像订批萨一样”疯狂采购避孕套的报道引发了轩然大波,而2000年悉尼人以为他们在奥运村里放了7万个保险套已经足够“保险”,末了却不得不再补充2万个以满足需求。从那之后,每一届奥运会一开始就准备好10万个保险套。“到处都有人在乱搞,”随队夺得北京奥运会金牌的美国女足守门员霍普·索罗说。拥有多项世界纪录的美国游泳名将瑞安·罗切特更直白:“我敢说有70%-75%的奥运选手都参与其中。你懂的,这就是游戏规则。”
“这是奥运村里真正的比赛,电视上可绝对不会播。”ESPN杂志的萨姆·阿里普尔在采访过美国队的历届奥运选手后,写下了这样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随时,随地
从开幕式之前一周左右,各代表团就开始陆续入住奥运村,而这“真正的比赛”也就此拉开序幕。“就像大学新生入学那天一样,”伦敦是水球队队长托尼·阿泽维多参加过的第四届奥运会,他对这套路早已不陌生:“你会很紧张,但同时又超级兴奋。大家都在跟其他人搭话,然后就试着勾搭上那个顺眼的伴。”
每个人对环境的适应顺序不一样,但餐厅总会排在头几站,于是在那里的奇观异景常常带给奥运新手们最大的冲击。“亚特兰大那年,当我刚进村时,就听到餐厅那里传来了巨大的欢呼声。”美国女足队员布兰迪·查斯汀说,“我们走过去,看见两个法国手球队员全身光光的,就穿着袜子、鞋和露屁股的那种运动内裤,还打着领带戴帽子,两个人坐在餐桌上面互相喂饭!我们当时就惊呆了。”
荷尔蒙的吸引力在训练馆达到最高。“姑娘们穿着轻薄的热裤跟胸罩,男孩子则只穿着内裤,”标枪帅哥布罗·格里尔说,“就算脸蛋是7岁的模样,身材也足有20岁的成熟。”在北京,体操跟水球还有柔道等项目的运动员在一起接受按摩理疗,于是体操队的青春期小姑娘也会试着跟其他队里的大男孩们调情。“我们的大多数社交生活都在那里发生,就在那个及胸的冰水按摩池里。”艾丽西亚·萨克拉莫尼当时20岁,她在美国女子体操队里扮演着“妈妈”的角色,她说她经常不得不制止小女孩们轻佻的发言。
有些教练会试图颁布禁令,禁止自己的队员们在晚上11点之后喧哗,也不准他们饮酒,美国游泳队更是严禁异性到访卧室。但这种事情永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拿过两金四银一铜的阿曼达·比尔德在悉尼奥运会时正跟队里的一名男游泳选手交往,根据她的说法,“反正大家都愿意走几英里的路,就为了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在这盛大的狂欢气氛中,运动员们仍需完成重大的比赛任务。“如果你不够自律的话,奥运村会让你完全乱了心神。”索罗说。有些人会禁欲到他的项目结束,也有人把性当做赛前的必要调剂。格里尔就属于后者:他同时跟三个女人纠缠不清,其中包括了一位曾经担当过火炬手的杰出撑杆跳选手,一个强势的跨栏选手,还有一个“极具天赋”的北欧姑娘。每一天,她们三个都会轮番造访他的卧室,有时候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来一位。“所以我在参赛时感觉很幸福,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彼此钟情的人,那一秒你的世界就完整了,在比赛场上的状态也会特别好。”格里尔的成绩证明了他的观点,尽管他在决赛时因为膝伤退赛了,但他在预赛时投出来的成绩却是雅典最佳。
等到奥运会的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项目落幕,混搭同居也成了家常便饭,很多间宿舍的门上都挂着袜子,大多数上过大学的美国人对此都不会陌生,这就是个约定俗成的信号,告诉你里头正上演精彩戏码,还有“快走开,别来打扰我们”。
结束征战的运动员们遵循本国奥委会的指令陆续离开奥运村,而他们空出来的宿舍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胜地”。在悉尼奥运会的最后八天,美国飞碟射手约什·拉卡托斯偷偷违令留在了奥运村里,于是他见到了人生中最混乱的景象:射击手空出来的公寓被寻欢的人们当做了“炮房”(他们真的就这么称呼它的),有人在门口摆了个行李袋,里面装满了从奥运村诊所里拿来的避孕套以方便进出的男女使用。“感觉就像我在奥运村里开了个妓院!”拉卡托斯说,“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放荡行为。”
都是寂寞惹的祸?
这一切即使不在大家的预料之中,但仔细想想,其实也合情理。奥运选手大多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多年以来,他们训练的强度堪比军队操练,而备战奥运时则更加孤独。“要想打上奥运会,你得每天从早上6点训练到下午5点,你觉得我们哪里能找时间约会呢?”阿泽维多如是说。
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就被放在一个可以免受记者和父母打扰的封闭空间里,身边满是自己的同类。所有人都有着黄金般的身体和较普通人更为出众的相貌,同样的刻苦经历则让他们彼此理解,索罗说这跟在酒吧什么的地方不一样,因为“在这里,搭讪变得很容易,你开头只需要问一句‘你参加的是哪个运动’,两个人就能迅速混熟。”
生理上的诱惑极难抵挡:在进村之后,许多运动员都降低了训练强度,但吃的还跟平时一样,他们每天依然摄入9000卡路里,但训练量却比平时低,于是多出来的精力就化作了人类原始的冲动。比赛之前由于兴奋而导致的睾丸素则进一步催化了这种欲望,按照美国泳将埃里克·尚蒂的说法,“整个奥运村都变得很狂放,像一口大锅一样将所有人吞没。”
更何况,无论你有着什么样的口味,奥运村都能满足你。女足姑娘?“都很性感,她们打扮得都跟摇滚巨星一样,”一名男游泳选手说;那男体操运动员呢?金特纳表示,“他们就像可爱的卡通小人。”虽然萨克拉莫尼必须看管着队里的小女孩别闹出乱子,但她自己毕竟也没能免俗:“说到身材,还是游泳和水球选手最棒,他们的锻炼全体现在上面了。至于搞径赛的那些家伙嘛,北京奥运BMX小轮自行车铜牌得主;虽然他们平时都挺严肃的,但一旦放松下来,他们就会显出招人喜爱的模样。”
也有人将这视作一次探险的好机会,因为在奥运村里的相遇注定只是露水姻缘,于是选手们都在追求各种挑战,比如说趁机接触截然不同的文化。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美国跳水队的传奇人物格雷格·洛加尼斯当时才16岁,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他就跟苏联的男孩们打得火热,还经常去对方宿舍参加聚会。他尤其震撼于苏联人对于性自由的诠释:“从文化上来说,他们要更倾向于公开展现彼此的亲密关系,而我着实被震撼了,因为当时我还在摸索自己的性取向。”洛加尼斯说他当时看中了一个苏联男孩,他蜷在对方膝盖上,两个人开始互相拥抱依偎,“我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安全感。”那场邂逅并没有下文,但对洛加尼斯的启蒙意味却不可小觑。1994年,洛加尼斯公开了自己同性恋的身份。
于是奥运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按照1994年冬奥会高山滑雪选手凯莉·谢恩伯格的说法,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极具奇幻色彩:“在这里,你可以赢得金牌,还能跟一个性感火辣的帅哥共度春宵。”
奥林匹克第二箴言
美国奥运选手的言论并非孤证。四年之前,曾称霸英国乒坛多年的马修·赛德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性与奥运之都》的文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证,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他在那两周半里所经历的欢爱性事比此前21年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所以每次有人问我说奥运村里面是不是就等于性爱狂欢胜地,我总会告诉他们这太对了。”赛德写道:“对于我们这些奥运菜鸟来说,巴塞罗那的性元素几乎与体育同样重要。”
在雅典,发到选手房间里的避孕套以每天1000个的速度消失;在北京,在奥运村诊所免费发放的10万个避孕套里,只有5000个在赛事结束后被官方回收。
还有更具体的例子:2008年,美国“飞鱼”迈克尔·菲尔普斯勇夺八金,打破了马克·施皮茨单届奥运独揽七金的夺金纪录,然后在大功告成的当天,他就被看到跟澳洲游泳女王斯蒂芬·赖斯在奥运村里卿卿我我。(当然,到了奥运会之后,他们也没有真的继续交往下去。)2012年,轮到了菲尔普斯的队友罗切特,在伦敦奥运首日击败菲尔普斯夺冠之后,罗切特跟另外一名澳洲女泳将布莱尔·埃文斯勾搭上了。“上届奥运会的时候我有个女朋友,那真是巨大的失误,”罗切特此前在接受ESPN杂志采访时曾这样说:“现在我又恢复单身了,所以伦敦一定会很棒。”
然而像罗切特这样敢说的现役选手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奥运参赛者对村中性爱这等敏感话题还是采取了回避态度。前几天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伦敦奥运村准备了15万个保险套,于是全世界的记者都开始追问运动员对这件事的看法,而运动员们则纷纷打起了太极。比如说百米王者乌赛因·博尔特就以自己“行程太紧”为由,表示“即使发了避孕套也没有对象可用”,而其队友阿萨法·鲍威尔则蹦出来一句,“我没用过,我还是处男呢”。
这么多年来,无数个奥运选手都遵守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在奥运村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能留在奥运村;巴塞罗那金牌泳将萨默·桑德斯说,“这就是奥林匹克第二箴言。”所以即使是在传媒与社交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有再多的爆料或是内幕都好,关于奥运村的秘密,外人所能窥见的也只有 冰山 的一角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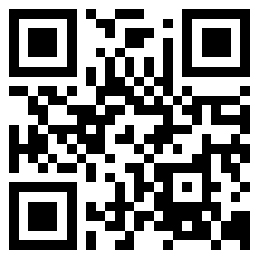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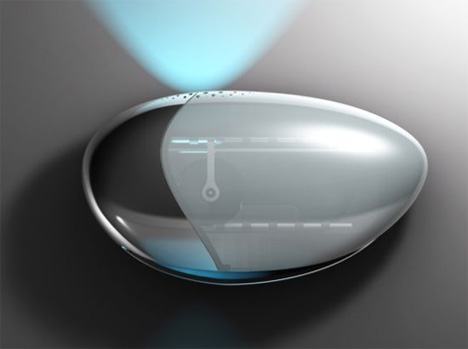 全球未来10大最酷洗衣机
全球未来10大最酷洗衣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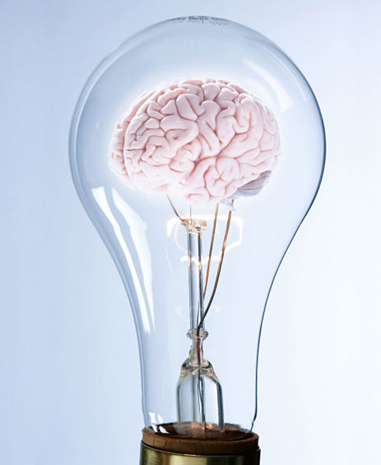 据说这46招能让你变得更聪明
据说这46招能让你变得更聪明 逆天了!这些发明居然是出自科幻小说
逆天了!这些发明居然是出自科幻小说 我们未曾在意的10项重要技术
我们未曾在意的10项重要技术  中国文化中的神仙都是怎么诞生的
中国文化中的神仙都是怎么诞生的 盘点全球八个最好和最差的电能来源
盘点全球八个最好和最差的电能来源 拯救地球10大新技术 沼气池也光荣入选
拯救地球10大新技术 沼气池也光荣入选 全球访问量最NB的17个网站,有你常去的吗?
全球访问量最NB的17个网站,有你常去的吗?
